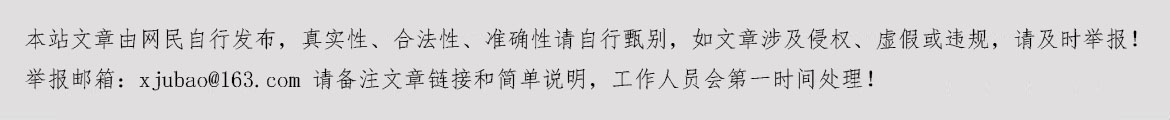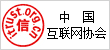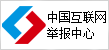漂泊在广州 一个中国女人和非洲黑人的离合故事
2021-08-28 19:34:01
我的姐姐票房 https://www.touzitop.com/xmzl/22095.html
六个月前,小芸没有给她45岁的非洲丈夫办签证,而是请求警察把他遣送回国。为此,别人都说她心狠。她心里清楚:自己实在是受不了。
过去的好多年里,就像小芸的丈夫一样,许多非洲人涌向广州。他们在这里淘金,甚至娶中国老婆,加深与这座城市的联系。
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来了。
相遇广州街头
小芸今年38岁。她22岁时离开家乡河南,在广东漂了16年。
早年她有过一次婚姻,那时她还没开始漂。和前夫在农村老家办了场热闹的婚宴,但是没有领证,没过多久就离了。
她的第二段恋情也只维持了一年时间。男朋友来自陕西,他们在广东打工过程中相识。交往快一年的时候,男友告诉她,他妈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一是嫌她远,二是嫌她是“二婚”。最后两人也分手了。
小芸一直钟爱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最早出来的时候,她在顺德一间电子厂里做流水线女工,加工小零件。一个简单的动作,每天重复1000多次。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枯燥而漫长,看不到头。
再加上每个月能到手的工资永远只有300块。不想被那种日子束缚住,她下定了决心离开。
广州三元里广元西路一立交桥下
失意的她拖着行李箱到广州寻出路。“广州不仅气候好,机会也更多。”她想着。“毕竟是大城市啊!”站在火车站旁车水马龙的路口,周围很吵,但霓虹灯的光很亮,她想追赶上这座城市的步伐。
小芸前后打过好几份工。她自知学历低。成绩不好、不想上学的她,只读到初中毕业就没往下读了。但是出来打工后,她想尽各种办法为自己“投资”。那时候电脑懂得少,她就报培训班学电脑,还学了设计。
“想着学好就能找个好工作。”报一个社会培训班,花掉1000多元钱,几乎是她半年的伙食费,她也不心疼。她从来不逛街,都是路过店铺时碰到打折才买。“看到好看的衣服,过去试一下,觉得便宜,才买下来。”她说。
后来,她终于找到了一份美工的活,坐进了办公室。然而,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那一行。“实在是太费脑子,太死板了。”她还做过一些跑业务的工作,卖保险、推销信用卡,时间都不长。
但是,在大城市呆惯了,有个念头在她的心里慢慢冒出来:她想在这里定居。这个外地女孩似乎已经忘却离乡背井的苦涩。“想一心一意赚钱,然后在这边买房子。”
没过多久,一个来自非洲的男人,改变了她原本的生活轨迹。
2004年初春,刚过完年回来没几天,在广州街头,小芸第一次遇到了这个尼日利亚人。那人恰好和她的朋友认识,在朋友的牵线下,两人慢慢熟悉起来。
从没有接触过外国人,她觉得挺好奇,同时也意识到这是个机会——可以跟着这个人学英语。这一契机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认识大约一年后,他们正式在一起。
“家里人知道后很反对,直到现在都反对。”小芸理解,但是她并没有太多的动摇。在她的印象中,丈夫话不多,但心地很善良。“走在路上看到乞讨的,一给就是10块钱。”她说。
合开了间外贸服装“夫妻档”
在广州三元里的广园西路上,他们联手开了一间做外贸服装批发生意的“夫妻档”。几百家档口里,小芸和丈夫的档口并不十分起眼。但这里是他们事业的“起点”。
每天,她的丈夫早上很早起来去市场找货,她在档口做生意。没过多久,她就能和客户用英语对话,虽然口音听上去有点蹩脚。
他们18平方米的档口,每个月的租金将近5000元。过来采购的客户基本是非洲人,要的都是“尾货”。一件T恤的批发价格不超过10元,牛仔裤不超过20元。这些“白菜价”的衣服每件只能赚几元钱。每个月得卖出足够多的衣服,才能够不亏本。
他们经历过外贸服装生意的红火期。2006年至2010年,中非贸易往来频繁,虽然签证政策越来越严,但仍阻止不了源源不断的非洲人从他们的故乡涌来广州。光顾服装城的非洲人,经常一次就拿上千件货。最多的时候,他们一个月的营业额能达到两三万。
当然,也会遇到一些难缠的客户。谈好的15元一件,1500件货全都打包好后,对方又改口跟她说14元。磨了好一阵后,对方仍不肯松口,最后她只得妥协。
还有一次,有个客户选货时把衣服在地上摆一大摊,乱七八糟。说好的全部拿走11块钱一件,最后又临时改了主意:只挑30件,还只愿意出10元一件。“全拿走10块钱可以,但是只要30件,没什么钱赚。”小芸跟那人说。对方听了,把货往旁边一扔,站起来就走。
时间久了,她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比如做这一行得会找货,有时候挑货时看走眼,货没买好,就很容易亏本。另外货放的越久,往往越卖不出去,也越不值钱。“所以,有时候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她说。
他们长期租住在白云同和的一个城中村里。因为商业繁华再加上靠近地铁站,一间两房一厅的民房,每个月的租金加上水电费要将近2000元。
不过,尽管有时候会觉得辛苦,想想生意还不错,丈夫也在身边,孩子出生后,家里也不像之前那样强烈反对他们的结合。她觉得松了口气。
唯一担心的是大儿子。“他不爱学习。”她说。“也许是我太忙,从小对他放纵惯了?”她觉得不解。花钱让大儿子学跆拳道,他半途而废。后来又让他学爵士鼓,他好像也兴趣不大。
再后来,因为身上没多少钱,儿子的这些爱好更是“搁置”了。
过去的好多年里,就像小芸的丈夫一样,许多非洲人被“淘金梦”召唤着,来到广州经商和生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在这里娶一个中国老婆,来加深同这座城市的联系。
然而,签证难往往又关上了他们长期居留的那扇门。
丈夫的签证续签常常让小芸觉得头疼。她感到广州对非洲人的检查变得愈发严格。“一次签证往往只有3个月、6个月、最长也就1年。”她无奈的说。“你不知道下一次去办的时候能不能通得过。”
尽管小心翼翼,2008年她的丈夫因为签证过期,被认定非法滞留广州,不得不交上一笔罚款后,回到尼日利亚老家。“我独自带着大儿子,等了他快五年。”他们拿到结婚证,已经是2013年的事。
他们做生意的那座外贸服装城里,四到六层全是密密麻麻的档口。“你在这里看到的中国女人,一般都是嫁给非洲人的。”她说,“纯粹是中国人开的档口很少,这一层只有三家。大部分都是非洲人或者是中非夫妇开的。”
她遇到过一个广东女人,对方当时一边哄着几个月大的孩子,一边告诉她:老公迟迟拿不到签证,平时只能在外面“找货”,只有周末才敢来档口,大部分时候,带小孩和做生意都是一个人。“不过,每个人的故事,谁又知道呢。”她又转移了话题。
赔了人家3万块钱
2013年春天,小芸的丈夫重新回到广州。那时,她对服装生意的前景还非常乐观。为了把生意做大,她在银行贷了十几万块。她想拼命挣钱,然后在广州彻底扎下根来。
然而,一连串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她的赚钱梦。
回来后没过多久,她的丈夫就“犯病”了。一天深夜,喝了酒的老公跑到一个陌生人的家里乱砸一通。他被抓起来,坐了三个月的牢。“被判赔了人家3万,都是我出的。”她感到无奈。
那次出事之后,她的丈夫被鉴定出来患有精神病。为了给他治病,她每个月都要花掉一千多买药。“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长。”这三年中,她的丈夫因为没拿到长期的签证,只得不停地回国。
后来,好不容易生活平稳,丈夫可以拿到一年的签证,她也再一次怀孕。那时她想:这下应该可以一起好好做生活、做生意。但她发现老公变得越来越懒了。“只会享受安逸的生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愿意干。”
她不太愿意再去回忆起那些不开心的日子,只是叹了气,“怀孕、生孩子期间,他基本没照顾我,而且花钱只知道朝我要。只会拖累我。”她说。
还没来得及细想,打击再一次接踵而至。在她怀孕5个多月时,父亲被查出来患有“多发性骨髓瘤”。去年10月起,她和弟弟为了给父亲做化疗到处筹钱。放疗一共花掉了50多万,她出了近一半。这之中有之前从银行贷的款,还有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到现在都还没还完。”她说。
同时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打击,最艰难的时候,她怀孕7个月还要大着肚子在档口拉客、卖货,甚至干一些重活。而生意却是愈发冷清,好像一天不如一天了。
“眼看生孩子的钱都没有,他却一点不着急,不操心钱的问题,更不会紧张我爸的病。”那时,因为拖欠两个月的房租,小芸还被房东下了最后通牒。
种种矛盾积累,她和老公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当众骂了他。“没给他面子,所以他又犯病了。”那之后,从去年年前到今年6月底,她老公都只在家吃饭、睡觉、看电视,基本没出过门。她形容道。
今年6月,小芸觉得实在受不了。她做了一个决定——没有给她45岁的丈夫办签证,而是等他签证过期后请求警察把他遣送回国。她盘算着,这样能省下5-6千块的机票钱,虽然代价是丈夫5年之内再不能来中国。为此,别人都说她心狠。她觉得很无奈,“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养不起’他。”
交不起租金熬不下去
大约2015年下半年开始,广州的大批实体店遭遇“关店潮”。小芸所在外贸服装批发城也同样未能幸免。“拉不到客户,不少档口交不起租金,熬不下去。”本就充满变数的道路变得愈发模糊。“回家的回家,转行的转行。”今年三月份,距离档口租赁合同还差两个月到期的时候,小芸退了档口。
不过,九月份之后,小芸又在服装城三楼另外租了一间档口。她想把生活努力拽回之前的轨道,期待转机出现。同一个地方,她发现,如今不少档口的推拉门都紧紧关着。她旁边的两家档口,只残余泡沫做成的廉价招牌。其中一家招牌上,手写电话号码早已字迹模糊,只剩一个缺了V字的LOVEYOU装饰还歪歪斜斜的贴着。
仍在营业的档口附近,零散地堆放着一些深绿色的蛇皮袋子,袋子里包裹着上百件T恤或牛仔裤,显得鼓鼓囊囊。更多还没有卖出的衣服,或是被绳子、铁链串起,挂在档口,或是像咸菜一样,堆叠在过道上。
她的新档口,在电梯旁的拐角处。本就狭窄的空间被一堵墙硬生生隔开,墙上贴着深红色墙纸,由于时间久远,边缘翻卷起来。一些墙纸出现破损,灰扑扑的墙面裸露出来。在管理处的特殊照顾下,她以每月1668元的仓库价租下这里。
小芸把样板一件件挂在旁边档口的推拉门上。她的好多样板都是从别人那里要来的。因为手头没有多少钱周转,她从别人那里拿了一袋货,给500块钱押金,卖出去后再把钱和对方对半分成。
前几天,她新进一批棉布女装裤,以每件6块钱拿的货,最后却只卖了4块钱。因为质量不太好,放了好几天都没人要,他们最多只愿意出3块钱。“亏死了。好不容易有人出4块钱,我只能卖。”她说。她觉得无奈的是:“现在来一个客户,都是要抢的”。
由于带着一个11岁和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为了节省房租开支,她搬去了离市中心更远的白云石井。
“学费年年长,把我的孩子逼到花都。”她还要承担大儿子私立学校每学期4000多元的学杂费。
她如今身上还背着好多债没有还完:做生意亏本的,父亲生病借的。她的银行贷款也因为无力偿还而逾期。
终是没能追赶上城市加速的步子,也没法追上每年似野草般疯长的房价。“赚不到钱,银行的信用也不好,买房已经成了一种奢望。”
“那么多年没有碰到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她回想漂在大城市的许多年:档口好像也没怎么赚到钱,都被丈夫折腾掉了。”她说。
在感觉最艰难的那个时刻,她开始在一个网络平台上卖辣椒酱筹钱。“都是为了生活。”最多时,她一天里会在朋友圈发布足足12条消息,都是关于辣椒酱的。她仿佛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一般。
然而,效果并不如她的预期。第一次只筹到795元,第二次更少只筹到433元。她自己额外添了200元,才凑够原本定下的项目目标金额,不至于筹款失败后让那笔钱“打水漂”。
大约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她会在趁晚上把小儿子哄睡之后开始做辣椒酱,备齐瓶瓶罐罐之后,她会让大儿子帮忙搅拌蒜蓉和姜蓉,她自己则去煮辣椒和鸡肉。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做出一大锅大约装15瓶份量的辣椒酱。
但卖出去的并不多。最多的时候,她一天也只能卖出三、四瓶。
客厅的简易餐桌上摆着一箱从淘宝上买来的车仔面,旁边是散落的酱料包。“那是给大儿子准备的。”因为做生意常常比较晚才能回来,大儿子饿了就自己煮面吃。她觉得愧疚,但也是不得已。
她常常想:如果辣椒酱能卖到一定量就好了。这个38岁的女人希望学习老干妈,把辣椒酱生意做大。
“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辣椒酱生意做起来。赚钱还债、养孩子、然后回老家过无忧无虑的平淡生活。”漂在广州16年的她没有把这里定义为她的家。她心中的那个家是河南老家,“还完债就可以抛开广州回家。”她如此描述。
虽然觉得翻身挺难的。但是她仍会安慰自己,“万一哪天又翻身了呢。”
她的那束希望之光似乎亮了一瞬又暗下去了。如今,最初的念想早已被生活磨平。不久前,因为生意没有多少起色,她新租的档口再次关门。
前几天,她久未见面的弟弟打来电话。电话那头,弟弟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这句话狠狠地击中了她,她想家,但另一种念头似一堵墙,横亘在她与弟弟的对话之中:“欠了那么多的债,还没还清,回去又怎么交待?”
她想快过年了,她大抵会想家,但她也特别害怕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