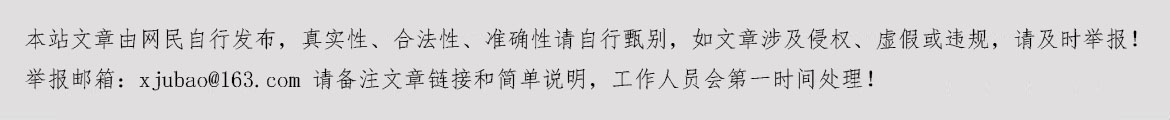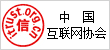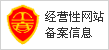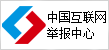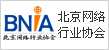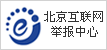揭秘:邓小平如何刚柔相济 处理对日外交事务
2021-05-28 18:01:02
原创 胡新民 摘自党史博采
图片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坚持把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辩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复兴之路。邓小平在对外交往方面的刚柔相济的处事艺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影响了交往国,影响了整个世界。1978年10月他对日本的访问掀起的“邓旋风”,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精彩序幕。
不失尊严地争取最大的外部支持
早在1974年至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就考虑到应该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语)。当时他经常会见外宾,那时他发现来访的日本人士,特别是日本经济界人士,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7年6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伊始,开始着手调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布局。他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他看来,围绕这个中心工作,在外交上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积极调整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最主要的就是调整对美、对日外交,特别是调整对日外交,这对于中国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更是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一方面,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借助日本力量不失为一条现实可行的捷径。当然,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对于地缘政治的战略布局也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日本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开启新的经济步伐的近邻中国,无疑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在这种天时地利的情况下,中日双方的互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日方针,并着力落实。其具体行动就是支持重开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1978年6月,中日双方代表团的谈判一时陷入了困境。6月5日,邓小平特意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明确表达了他的态度。他说:“我们双方只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比较容易解决。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两国间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曲折,但我们是休戚相关的,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在政治上体现出来,就是尽快地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相信,我们两国发展合作的前景是良好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朋友的帮助。”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8月12日,中日关系史上第二份重要的政治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顺利签署。这份文件既是之前中日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之后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一个新起点。
图片◆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图为邓小平抵达东京时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1978年 10月22日,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日本进行的访问,受到了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10月23日晚上,在日本首相福田纠夫举行的宴会上,邓小平在向日方陈述了此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日友好外,还特地说道,他要像中国古代的徐福一样,寻找“长生不老药”。邓小平这个比喻立即引起了在场日本人会意的笑声。邓小平继续解释说,他说的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实际上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10月27日,邓小平参观了京都的“二条城”。日本友人介绍道:“您在此看到所有文化都是我们的祖先从中国学习而来,随后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逐渐改造而成的。”邓小平立刻回答说:“现在我们的地位(老师和学生)颠倒过来了。”
日本各大媒体对邓的访问活动作了大量报道,称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邓旋风”。尽管邓小平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是寻求日本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但在言行上始终体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风范。日本最有影响力的NHK公共电视台对邓小平访问日本工厂的报道就很有感染力。NHK的报道给观众呈现的是一个精力充沛、观察力敏锐且充满自信的邓小平。邓小平在参观中亲眼见到日本先进技术,并对此充满了热情和好奇。但更引人注意的是,邓小平并没有任何谄媚奉承之举。美国著名的中日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评价道,邓小平的日本之行既承认了外国先进科技的价值,又没有牺牲中国人的尊严。
图片◆记者招待会上的邓小平。
但是,中国想借助外力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是曲折的。“大规模引进”,即后来称之为“洋跃进”的建设热潮很快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和一系列其他问题。1979年4月,中央决定对一些引进项目(当时日本项目占大部分)停建、缓建。对此,日本方面反应强烈,指责中国“毁约”。经双方多次协商,后来根据中方建议,日本同意提供大规模的条件优惠的日元贷款,从而恢复了一些项目建设。在“毁约”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并没有向日本方面表示道歉,而是直率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遇到的不过是暂时的困难而已。当时中日不少有识之士对邓小平的表态表示了理解和佩服。因为中国出现这样的困难,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中日双方都有责任。作为当时实际主政的邓小平的坦然淡定的态度,使世人感觉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实事求是、不卑不亢的风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邓小平的这种表态丝毫没有减少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魅力,可以说后来日本的各界人士对邓小平仍然是一如既往地尊重。2007年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有媒体报道说,当年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时,日本整个国家为之震动——去世之日,刚好日本北海道发生地震, 震级不大,这在日本是家常便饭,可还是有人说确实是“巨星殒落”,天地感应。那些天,日本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邓小平。
在寻求外国贷款这种看似是求人之举的问题上,邓小平在战略上的知己知彼和在战术上的刚柔相济相结合,总能使中国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他在1978年6月23日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就说:毛主席历来主张自力更生,但不排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毛主席历来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洋为中用是自力更生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
图片◆10月24日,邓小平参观尼桑生产线。
后来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最多的优惠贷款。无论是哪个国家贷款帮助了中国,中国都会也应该表示感谢,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等于一方就是完全的施惠方,而另一方就是完全的受惠方。对于日本来说特别如此。除了前面提到的日本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外,还有因为当年日本想要成为国际大国,而必备的指标性条件之一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数有关。邓小平在适当的场合总是明确强调,这种贷款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谈到中日两国经济合作问题时指出: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1987年6月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更是直率地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
毫不含糊地批评日本国内的右倾化思潮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1981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很快,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经济合作日益加强,经贸关系日益扩大,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重视。1982年9月28日,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铃木善幸时,他总结说:中日关系有许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的长期国策。
但是,此时的日本民族自尊也越界进入民族主义的傲慢。态度激烈变化的一个早期表现是在1982年,当时文部省在它检定的教科书中试图以“进入”来取代“侵入”,以美化日本二战期间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还试图删除或淡化日本的战时残暴行为。此举引起亚洲国家以及不少日本人的愤怒。作为主要受害国的中国,更不能无动于衷。
图片◆1982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铃木善幸。
邓小平从来就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因此,当日本国内出现这股右倾化思潮的时候,他毫不犹豫,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在1982年9月28日与铃木善幸会见时,除了强调中日友好,还毫不含糊地指出:中日两国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完全一样,这也是正常的。类似教科书这样的问题今后还会有,还是要在相互谅解的精神下,继续解决发生的问题。就中日关系在政治上的问题来说,我们希望阁下和阁下的政府以及以后的日本政府,还是要注意军国主义倾向。我们不是怀疑日本政府有这样的倾向,因为你们的宪法有明确的规定。但日本确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想复活军国主义。
在1982年一年,除了与铃木善幸会见外,邓小平还曾六次谈到过这个方面的问题。
1982年7月29日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廖承志、姬鹏飞、黄华、邓力群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问题。指出:这个问题要抓。要针对他们所说的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所谓“内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活动说成不是侵略。要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驳倒。今年“八一五”,《人民日报》要写纪念社论。强调中日友好及其历史渊源,中间要有日本侵华的一段。在中日友好的长久历史中,只有一段短暂时间不愉快。问题是要对这段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能也不允许进行歪曲。只有如此,中日两国关系才能按正常轨道前进,中日两国友好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1982年8月10日上午,邓小平同邓颖超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牛满江、葛守仁、聂华桐等人。在谈到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因为好多年没提这个历史问题了,这个题目出得很好。我们的娃娃不能只知道友好,还要懂得历史。最主要的是教育人,包括教育日本人。
图片◆1982年,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四川访问。
1982年9月18日下午,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乘专列赴四川访问途中,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上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
1982年10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谈到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时说:我们为什么对教科书问题这么注意?因为在教科书问题上有一个教育日本后代的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呢?所谓世世代代,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只是下一代,还有好多好多代嘛!所以,我们提醒日本,有那么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兴风作浪,我们双方都值得警惕。
1982年11月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宇都宫德马为团长的日中友协代表团。在谈到日本修改教科书的问题时说: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恐怕更大的问题是教育后代问题,是通过教育把后代引往哪个方向的问题。教科书问题实际上有军国主义的影子在作怪。日本确实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
1982年11月16日上午,邓小平和王震会见小柳勇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友好之翼访华团领导成员。邓小平指出:社会党的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对许多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最近,贵党在教科书的问题上,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精神,我是非常赞赏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得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的,是有深厚的基础的。教科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问题的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历来是存在的。我们不是讲执政党、政府,但作为一种思潮,战后是一直存在的。既然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不能不对这种思潮、这种倾向提高警惕。
日本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发展迅猛。与其相伴的是日本相当一部分人因感到日本财大气粗而变得目中无人,一度对美国都敢口出狂言,对中国就更没有放在眼里。日本国内的右倾化思潮愈加严重,日本朝野不时有人公开否认对中国的侵略历史。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都对日方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1983年9月1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谈到日本扩大防御计划问题时说:我们历来不反对日本拥有自卫力量,但应该有个限度。日本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它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还进一步提出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的含义是什么?日本想在一千海里内承担军事义务,这个性质就变了。
在后来1986年8月5日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1987年5月5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和1987年6月4日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邓小平都在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性同时,严肃地批评了日本国内日益严重的右倾化思潮。
在1987年4月6日会见瑞典首相卡尔松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更是郑重指出: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中国,十分蛮横、残酷。由于有过这段经历,所以我们对日本有斗争,但斗争非常克制。经过这些斗争,中日两国人民理解更深了,从而使中日关系更加成熟。
图片◆1989年9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
1988年4月19日上午,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首相特使、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说:我们两国的关系一般来说还是正常的。但最近这三四年,从教科书问题开始,总是不断发生一些麻烦。值得指出的是,你们称为右翼势力的极少数人,他们的活动应当引起警惕。如果对这些活动处理得过分软弱,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中日友好。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孤立起来看并不大,但积累起来就代表了一种倾向,一种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这种破坏力量的所作所为势必要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反应。我知道,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是不赞成这些事情的。国家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是要根据两国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和最近十几年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经验,妥善、及时处理遇到的问题。为什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很重要,不能忽略这个问题。针对一位日本议员提出日本不存在极右势力的观点,指出:存在着极右势力,任何社会都存在。周总理诗碑对日本有什么坏影响,为什么要破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段历史,为什么修改?这是有目的的,无非是煽动日本人民搞点什么事情,散布敌视中国的思想,是想在日本恢复点什么东西嘛。从三岛由纪夫那件事就可以看出一种倾向。邓小平在这里特地提到了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三岛由纪夫是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军国主义团体“盾会”会长。1970年11月25日,他到东京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军总监部发表演讲,要求修改日本宪法,使自卫队成为日本真正的“国家军队”,以“保卫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然后剖腹自杀。邓小平在日本国内右倾化思潮日益泛滥而中日两国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的时候,提出了这件发生在十八年前的事情,其警醒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意图不言自明。
邓小平宣布告别政治生涯是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宣布的。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说:在我离开领导职务之际,应该见见老朋友。你们这个团可能也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在谈到中日合作时说:两国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对中日友好的方针不会改变。希望日本方面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友谊才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
邓小平访日期间精彩的“话中话”
每当我们观看邓小平访日的影像资料时,他在乘坐日本高铁时有段话令人难忘。那段影像的对话打出的字幕是这样的:问:“怎么样?乘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想法?”邓:“我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当时全程陪同邓小平的中江要介先生后来是这样回忆和评价的。
在从东京到京都的“光号”新干线列车上,他问邓小平:“现在时速是240公里,您感觉如何?”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这对于中国太快了。”接着说:“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中江说,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既表达了“要让国家迅速发展”的迫切心情,也指出了办什么事也不能过于着急,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的道理。
图片◆当年乘坐新干线列车前往京都的邓小平。
现在回头看看我们这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今天中国自己的高铁建设的成就,就不能不感觉到邓小平的话寓意深长。不过,有些一直生活在国内的人可能并没有感觉到那么深切。局外人有时反而感觉更深一些。傅高义就感慨道:“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拍摄的纪录片曾令中国人瞠目结舌——工厂、交通和通讯,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具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而今天,这一切在中国已变成现实。”
圆满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当时是中日两国的首要任务。因此事先中日双方商定,邓小平这次访问,不讨论诸如钓鱼岛归属那样有争议的问题。但在东京的那次有400余名各国记者参加的记者会上,依然还是有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关于钓鱼岛的问题。邓小平回答的全文(据影像字幕)是这样的:“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就有叫法不同,这点双方确实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样的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就中国人的智慧来说,也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些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两国政府谈这些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你摆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图片◆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等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换仪式上。
现在来回顾一下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前的中日双方对待钓鱼岛等棘手问题的情况,则更能领会邓小平刚柔相济的处理难题的艺术。
中方一直认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日本方面则认为是日本固有领土。中日双方谈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都有自己的原则主张。日方的五项原则主张之一是:“关于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该群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鉴于现今实质上处于我国的管辖之下的事实,我方要坚持这一观点。”(见《回顾九十年——福田纠夫回忆录》)。
日方长期以来也是完全了解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的,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日本政治家中的某些有识之士的观点起到了积极作用,才使中日双方在敏感期间都默契地“不涉及”。日本著名政治家,1974-1976年的首相三木武夫的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道:“日中对立破坏了亚洲,日中友好将建设新的亚洲。历史证明着这一点。日中双方当然各有各的立场。但仅仅强调立场的不同,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超越不同的立场来寻求共同的利益,使邦交正常化,并筑起友好和合作的道路,才是在政治上应负的责任。”(见《三木武夫及其政见》)
邓小平的话实际上是向国际社会宣示了这样一个声明: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双方都是同意“不涉及”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个钓鱼岛问题是双方同意“搁置”起来的。邓小平讲完那段话时,当场就博得了全场掌声一片。有人评论,这相当于对刚刚生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第一款中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的实例解释和说明,具有官方文献和公告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多年,日本官方也从来没有对邓小平当年的讲话提出过异议,这在无形中增强了“搁置争议”之说的正当性和真实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邓小平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做到了“绵里藏针”“滴水不漏”,从而达到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国家间战略互惠的最大效果。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停滞了二十余年。中国经济尽管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的趋势还是高歌猛进,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各个层级的政客在焦躁中不断对中国挑起事端,钓鱼岛终于成为了热点中的热点。形势今非昔比。
傅高义在2011年出席日本“关西·大阪文化力会议”时说,邓小平对日友好的战略令日本在80年代“拼命援助中国实现了现代化”。2013年9月,傅高义在日本东京都就中日关系发表演讲。演讲后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谈到了对解决钓鱼岛领土纠纷的看法。他认为双方已不可能回到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主张的搁置争议状态,应探索保全面子的解决方式,指出“日方有必要寻找可使中方认可的主张”,通过首脑对话等摸索出路。